
希望热线-生命教育与危机干预中心

希望24热线小助手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 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加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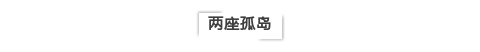
李宙是一名监狱警察,他负责惩罚犯了错的服刑人员。说起来有些不愿意,但武器和权力,还是在李宙们手里。
他容易对服刑人员产生同情,从根本上说来是对人类命运不公平的感慨——无法预测的灾难、充满压力的生活变故和社会支持在整个社会中并不是正态分布的,那些弱势群体面对的变故更多,获得支持也更少。
随着灾难和变故而来的巨大痛苦在某些极端情境里可能伤害他人——犯罪,也可能伤害自己——自杀。
同情让李宙痛苦,这和他的职业角色有冲突。为了寻求一个解脱的途径,每次离开监狱,李宙都会驱车 40 公里,来到希望 24 热线在南昌设立的自杀干预热线,希望抚慰那些正处于巨大的变故和痛苦之中的人们。
监狱之外的这个 15 平方米的密闭空间,就成了李宙进行身份转换的地方。2012 年,台湾人林昆辉在上海成立了一条自杀干预热线,由持有心理咨询师执照的志愿者来完成接线和自杀干预工作,热线发展壮大,陆续在中国二十多个城市开展起来,李宙是志愿者之一。
南方的天气大多湿润温热,从监狱到接线室的途中,会经过他从小就熟悉的街道和树木,树木高大地几乎遮住了整条片天空,阳光透过树叶照在路上形成渐次变化的阴影。
接线室只有 15 平方米,两台电话用于随时接通有自杀倾向来电者的倾诉,两张床帮助接线员度过深夜,一株植物摆在窗台上,窗外是一堵墙,抬头只能看见天。
在这里,李宙说他学会面对自己,面对人类。
那天晚上不到深夜,10 点左右,那是一个说话声音低沉缓慢毫无生气的年轻女孩,一来就问「人活着是为什么啊」,此刻她正躺在宾馆的床上,作为医生的女儿,她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快速死亡。
「可以跟我说说你遇到什么了吗」,「你的家人呢」,「你太辛苦了」,「你喜欢玩什么,什么能让你开心」,这是接到电话的接线员从技术层面出发对来电者说的一些话,她尝试拉住她,但对方最初总是拒绝。
这个女孩前一天打过来一次电话,差不多的时间,差不多的声音,那时候她一个人在家,还没有准备好工具和药品。抑郁症让女孩无处可逃,你能拉住她什么呢,挂掉了昨天的电话,今天的绝望仍然存在。
「我喜欢弗洛伊德,我喜欢研究潜意识,可是我自己还是救不了我自己」,「流血了,好痛」,「你们不要救我,把我埋葬了就好」,「不要阻止我,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不会告诉你我在哪的,你们会报警」,「我知道你只是志愿者,却为我操碎了心」。
情况危急,但对对方的情况完全无法控制,接线员在电话这边泣不成声,女孩说:「你对我真好,我喜欢你的声音」。
只有一根电话线,没有电子追踪系统,没有医院,没有警察,两个人就像两座孤岛。
「你先坐起来好不好,我们不要躺着了」,「你先止一下血好吗」,「我可以叫你妹妹吗」,女孩又抗拒,又接受,本能给自己止了血,保持和接线员说话,「我好想抱抱你啊」。两个人互相拉动彼此,约好以后一起去爬泰山。
电话持续了一个小时,这时女孩那边另一个电话响起,有人敲门。有人找到她了,她警觉起来,开始对着接线员破口大骂:「你混蛋,我不该相信你」,「我忘了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永远不会有背后的友谊」,「你们要我怎么活着走出去?」,电话在女孩的激烈情绪和一片嘈杂声中中断,接线员放下电话,情绪仍然没有平复,夜也没有太深,但对于接线员来说,任务算是结束了,不必面对一个人死在面前。虽然,她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有时候,铃声不间断地响起。尤其在深夜,人们总在那个时候更悲伤。
自 2012 年 12 月开通以来,希望热线已经累计接通了 16 万通求助电话。这其中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人们面临的烦恼来源在常见的爱情、财务、工作、婚姻、自我、孝养之外,更高比例是「不详」。16 万通电话里,有 0.1% 的人处于最高危级别的情况——他们正在实施自杀行为。
自杀这个伴随着人类一直存在的远古命题,从来没有被真正「攻克」过。加谬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 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 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世界上每年大约有 100 万人死于自杀,每 40 秒钟就有一人死于自杀。
2002 年,客居中国的加拿大精神科医生费立鹏开启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自杀研究,上个世纪末,中国自杀率高达十万分之二十三 ,是 15—34 岁年龄段人口的首要死亡原因。每年因自杀夺走了 287000 中国人的生命, 中国也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天,李宙先是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一来就说想杀了自己父亲。倒不是什么大事,这位年轻男子脸上长了一个东西,父亲说可能是痤疮,他觉得父亲在诅咒自己,就想杀了他。男子语速有些快,说话开门见山,李宙对他不陌生,印象中已经接过几次他的电话了,每次一来不是要自杀就是要把父亲杀了。
对李宙来说,应对这个人不算难,5 - 10 分钟,不和他争论父亲的对错,像哄小孩子一样,「真棒」,「还好你能开导自己」,「那我们去医院咨询专业的医生好不好」,「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去医院呢」。
根据李宙学到的技术,在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否认对方的情绪,即便他看起来暴力又疯癫,你要让他感受到「现阶段我这样就是我最好的状态了」,就像一个人在哭泣的时候,最忌讳的安慰语是「你别哭了」,哭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最好的事了。
这显然不像一个狱警该做的事,狱警从来不会这么温柔。前一天李宙还要眉头紧锁面对铁栅栏后面的服刑人员,今天就变成了一个慈眉善目的陪伴者,要对一切悲伤的愤怒的邪恶的念头照单全收。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还有别的家人吗?」,「你平时喜欢玩什么呢」,「噢!你喜欢音乐,我也喜欢音乐」。
在这里,李宙有时候 40 岁,有时候 30 岁,有时候姓李,有时候是学法律的,不管是眉头紧锁,还是慈眉善目,在李宙看来都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技术指导来实现的。
希望热线创始人林昆辉开发了一套干预自杀的方法,被称为「非事件量化 S-R 心理咨询与治疗学派」,这套方法的核心是不要陷入创伤者的困境事件中,也不要试图帮他解决问题,而是协助他「从沉迷于过去创伤事件及当下创伤心理循环的黑洞中跳出来」。不评论事件对错,给他肯定,包括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监狱里也会遇到服刑人员自杀,遇到犯人冲动的时候,监狱的方法是把他隔离起来,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作为惩罚,也让他没有条件自杀。这是一个合适的方法吗,李宙不知道,现状有些尴尬,监狱也有心理咨询,但并不太能系统得派上用场。对于自杀的干预,李宙是希望能把手段放在更前面的部分,消除人的烦恼,他或许就不会有自杀的想法了。
接完电话以后,李宙就又恢复了冷静的模样,重新开始播放手机里的心理学教学视频,他还在惦记知识和技术上的补充和修炼。李宙不愿意表露出哪怕一点,这套在他表达里完全理性可控的技术方法,其实是饱含温情的。
李宙有一个稳定的来电者,他的妻子,他也重复告诉妻子,遇到任何问题,都要随时给他打电话,他其实从内心相信这个电话的力量,他在高中毕业之后有过不那么快乐的几年,现在他时常会想,当时如果能有一个人听他这么说话,他或许不会困惑那么久。
人就是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陷入痛苦中,快乐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有一些人任痛苦摆布处置,有一些人则还存有一丝力气和痛苦抗争,李宙和他的同事们在漫无边际中伸出一只手,不知道能抓住多少人,能抓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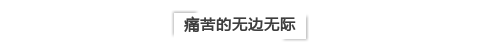
李宙接的是赵子君的班,赵子君是南昌地区接线时间最长的接线员,做了 26 年肿瘤科护士,见惯了人类面对死亡和疾病时的无能为力,通过自杀干预热线把人从死亡边缘救回来,能让赵子君免于恐惧。
她喜欢在接线室待一个通宵——高危自杀案件总喜欢发生在深夜。
即便已经接了两年电话,听过了无数人痛苦,但痛苦本身的不着边际有时候仍然让赵子君震撼。
现代社会趋向于让人的痛苦社会化,制度也试图把人的痛苦放在纳入自己的管理范畴,比如在一场灾难里,人的痛苦是社会性的,可以通过预防、报道、救灾和哀悼这个流程来解决。但在美国人类学家凯文博看来,人身体和心灵的苦痛一定都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灾难是无法预测的,人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不确定的,种种痛苦都是崭新、敏锐又不确定的。灾难可能完全来自命运。
在这个 15 平方米的房间里,人的痛苦,也是无边无际的。
「玩得好的朋友走了,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一,他们说我是想象的」,
「想自杀,初二割腕」
「喜欢的女孩跳楼自杀了,我也不想活了」
「和女儿的老师发生性关系,被女儿发现」
「看见孩子聊天信息中有『老公,你去上学了吗』,想和孩子谈,但张不开口」
「因感情问题导致工作失误,去咨询心理医生,没帮助,今天早上就想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
有时候,它们隐密又禁忌。
「结婚一年多,老公一直穿女装,胸大,比较女性化」
「17 岁男生,喜欢穿妈妈的黑丝袜」
「有钱人家的保姆,双性人」
「喜欢女性卫生巾,喜欢妈妈的卫生巾」
「用旗帜自慰,做过心理咨询,没用」
一位 13 岁的男孩问,「两年前被继父玩弄小鸡鸡,这种行为对不对?为什么过程中小鸡鸡会硬起来」
痛苦有时也细小又微妙,无处遁形。
一个小学生打来电话,他告诉接线员,自己练习跑步一年了,365 天,跑遍了各种天气、各种白天和黑夜,从没有间断过,在他的脑海里,他已经排练过无数次在学校运动会上加速、冲刺、夺冠了。终于等来了运动会,他就像每天的训练一样,完美完成了比赛,拿到了冠军。但他却非常伤心,一切就像在这一刻结束了一样,没有人来称赞他「你太了不起了」,积蓄了一年的努力在他跨过终点线的那一瞬间就失去了意义。
有的故事戛然而止,比如一个误入传销组织的退伍军人,或者一个爱上易中天的姑娘,在说完「你根本不懂我的痛苦」后就挂掉了电话。
一个小城男性,得了 12 年抑郁症,又会被如何看待呢?这是赵子君接到的第一起自杀高危来电。「40 来岁,听起来很壮实,在超市打工,和老婆离婚了,孩子扔给养父,养父不理解,怎么可能抑郁呢,就和他断绝了关系」,赵子君接到电话时,他正坐在宾馆的房间里,药品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在中国人坚固的「过日子哲学」语境下,这位男人「浮生取义」的行为没有丝毫正当性,即便他已经把痛苦细细研磨了 12 年,从前没有用,将来或许也没有用,只等待在这一瞬间释放。
释放之前,他还是遇见了赵子君。无论他遭遇了什么事情,赵子君在电话这头都像最后一根拉他的稻草一样,不断告诉他:「我很在乎你」。
关于抑郁症的根源,研究者认为它有一些决定因素:人类不幸的社会根源造成了绝望、去道德化、自认失败的人格和处境。
男人向赵子君陈述了自己的痛苦,央求赵子君给自己的养父打电话,自杀是他最后博弈的武器,就像羸弱的人撞不破一堵墙,于是抱着炸弹和墙同归于尽。
在南昌的深夜,赵子君拿起自己的手机,拨打了男子养父的电话,这是一个违规操作,接线员不被允许暴露自己,但赵子君已经顾不上了,男子的死亡可能就要发生在她的眼前。但现实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千钧一发,赵子君拨通电话,对方接起来,是难懂的方言,对男子的死亡没有太大兴趣,很快就挂了电话。
有一件事情,男人只告诉了赵子君一个人,这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生活中该跟谁诉说呢,他有偷窥癖,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在女厕所,在所有有女人的地方,偷窥带来的痛苦大于了快感,他认为自己是卑鄙的无耻的,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是自杀。
性有一套自己的逻辑,成为人类广泛痛苦的根源之一。接线员时常会面临对方讲述自己因为性而遭受的痛苦,乱伦的、出轨的、性侵的、性幻想的,运气不好的时候会遇到性骚扰,打电话来的人听着你的声音进行自慰。有的接线员会因此苦恼,挂掉电话,回家呕吐,放弃工作。
而这个男人让赵子君知道,性的焦虑也是需要被接受的焦虑,它或许是对生命产生焦虑的源头。
赵子君也接到过乱伦电话。深夜,一位男性打电话过来向赵子君倾诉自己和母亲乱伦的烦恼。这种来电并不少见,有些是幻想,有些确是实际正在发生。但在深夜,欲望和负罪感会从心底被翻出来。
大多数情况下,儿子与母亲的乱伦发生在父亲离异、去世或者长期缺位的情况下。「这一类孩子他从小是跟母亲一起生长,与母亲的连结是很紧密的。婴儿时期,无论男女跟母亲都是共生的状态。随着这个婴儿长大,他是需要分离的, 比如上幼儿园,这是第一次分离,一直到后面上大学进入社会,都是一次又一次分离,有一些母亲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与孩子紧紧缠绕,没有做到很好的分离。」
打电话来的男人在 16 岁时父亲去世,他希望能照顾母亲,希望能给母亲更多的爱,在和母亲保持十几年性关系,如今已经娶妻生子的情况下,和母亲仍然未了断的关系让他十分痛苦焦虑。赵子君肯定了他的爱,但告诉他不应该是性爱,不是取代父亲的位置。
但赵子君并不能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我们只处理他的焦虑情绪,我们也没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还是要让他自己去抉择。他打电话过来还是想倾诉,我们在听他诉说的过程中,对他同理,他的焦虑已经缓解了一大半了。」
赵子君始终认为,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是应该被接纳的,即便它们有时候看起来荒谬、不道德、充满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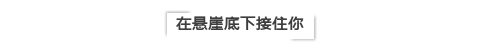
有人打电话来对着她发火把她骂得狗血淋头,赵子君对他说:「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苦,你遇到了这么多烦恼的事情,你朝着我大喊大叫也是可以理解」,一说完,那个人愣了几秒,反倒就平静下来了。「他的愤怒不是朝向你的,他可能积压了很久找不到出口,我们就成了一个出口。」
痛苦不仅有它社会性的原因,也会产生社会性的后果。在赵子君看来,没有出口和不被接纳的痛苦,对个体而言,就会演化成自杀。
所有的接线员都被要求挂了电话,离开接线室之后,就把这里的事情都忘掉,他们必须适应自我在两种身份中切换,不要陷入这些事件里面,就像赵子君并不会多想和母亲乱伦的男人之后会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
林昆辉自己也认为,自杀干预热线在整个自杀干预系统里是很薄弱的一环,它甚至算不上解决了最高危人群的问题,只有一些次高危人群会打电话过来。
自杀这一复杂现象, 从来都是由多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的, 因而世界上的自杀干预项目虽然很多, 但哪些确实降低了自杀率, 却无法厘清。
对于自杀干预热线的有效性,至今也没有量化的数据,但赵子君们相信,危机是有时效性的, 是暂时的失衡, 且人自身有复原能力,自杀热线的存在可以为许多孤单和失望者提供帮助。
中国的自杀人口格局不同于欧美和其他发达国家,后者的自杀人口 90% 来源于精神疾病患者,中国只有 50%,因此在中国 , 社会文化因素比精神疾病因素更重要。
造成人类不幸和痛苦的宏观社会根源得到显著改变时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农村人口得以实现流动,以及自杀药品(农药)的控制,中国的总自杀率尤其是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开始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杀干预项目的无能为力,无法预测的灾难、充满压力的生活变故和社会支持在整个社会中并不是正态分布的,那些弱势群体面对的变故更多,获得支持也更少。自杀热线可能是他们在陷入极端心理困境时最易得的求助途径。
中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是由加拿大人费立鹏 2002 年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开通的,林昆辉的这一条,是在 10 年之后才开通。他和费立鹏见过一面,「费立鹏是精神科医生,我们救人的心都是一样的,但是方式不同」。
有那种真的因为电话被拯救的人,他们本来站在窗户边,或者手里拿着利器,命悬一线,他们在电话里大哭,接线员有时候也泪流满面,但是就不管不顾地,使劲拉。
赵子君接到过一个来电,在大多数人都睡了的深夜,一个睡不着的男孩打过来,告诉赵子君自己担心即将到来的考试。来电显示,这是一个重复个案,来电者曾经打过来求助过,上一个接线员备注对方有「公务员考试情结」。
这是一个孤注一掷,辞掉工作考公务员的农村年轻人。前三次都没考上,马上要考第四次了。
赵子君的职业敏感告诉她这可能不是单纯的考试焦虑,一步一步问下去,男孩告诉赵子君,他在考试前进行了一个体检,体检发现他心动过缓,每分钟心跳只有四十几次,现在两次心跳间隔 0.12 秒,如果间隔达到 0.4 秒,他的心脏停跳就不可能再恢复了,医生要他立刻装心脏起搏器。
他无法接受医生的建议,害怕单位不会录用他,害怕谈恋爱结婚时会有影响,害怕不能坐飞机,他考虑种种情况,一直拖着不去装。但如果不装,他又担心自己有一天心跳停止。
赵子君说:「我明白了,你之所以睡不着是因为你害怕睡着,如果你睡着,你担心这个心跳会停止,你担心你睡着之后明天早上起不来」,对方一愣,他可能随时会死掉,这是他真正焦虑的事情。因为这个焦虑,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怎么睡觉了。
「我是学医的,我可以很肯定地跟你说,这是一个小手术,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痛苦」,赵子君从医学技术的角度安抚了他,也告诉他谈恋爱、找工作、坐飞机,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她告诉他,从 0.12s 到 0.4s,其实还有足够的时间,他完全可以安心睡上一觉。电话持续了一个小时,赵子君确实通过电话治愈了这个陌生人,话还没说完,男孩就在对方睡着了,赵子君挂掉了电话,替这个一个月没睡觉的年轻人松一口气了。
卡夫卡说:「有天堂,但没有道路」,我们大概都知道美好生活的模样,但不知道如何走过去。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人员也并不提供道路,「我们只是在悬崖底下接住你」,赵子君说。

南昌的接线员大多有平稳幸福的生活,不接线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家庭里度过,理解自身,日复一日走在南昌的香樟树下,接线的时候他们就钻入另一层空间,去理解世界,为让世界更美好尽一点绵薄之力。
有人在成功接完一个高危电话后精疲力竭,埋头痛哭,也有中途放弃的人,电话那头的痛苦恰好击中了他,他不敢再面对。
晓笙是一位中学老师,家在离南昌 120 公里外的抚州,每一次她都提前订好第二天最早一班火车,赶来上一个早班,有时候和李宙接班,有时候和赵子君接班。晓笙喜欢说:「来电者用他的痛苦滋养了我们」,不然,我们哪里有机会知道人的痛苦和命运是如此复杂。
每个接线员都接过高危的自杀来电,晓笙也接到过。一个走投无路,事业「失败」,又患有抑郁症的男人,写好了遗书,取出了股市的钱,安顿好一切,准备跳到长江里去。脑袋里的魔鬼在推他,晓笙就和脑袋里稍显弱势的天使一起拉他。
终究还是拉回来了,男人对晓笙说:「真的特别感谢你,这句话我都没有对医生讲,也许医生对我这些都不感兴趣,你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这么用心的陪伴我,我特别感谢你,我一定会活下去」。
晓笙想起自己小时候,不到 5 岁,有一次不小心掉到井里了,有一个陌生人,想尽了各种办法,把她从井里拉出来。她一直没有机会去感谢这位救命恩人,还没能请他吃个饭,他就因为意外事故去世了。晓笙觉得很遗憾。
30 多年过去了,这个画面一直在她心里,晓笙现在总把人从生死边缘往回拉,就像当年那位陌生人把她从井里拉起来一样,「我现在想想觉得挺温暖的,他给我第二次生命,对这个社会而言,他其实拉我是值得的。」
赵子君大多数时候都很稳定,她有扎实的知识和技术,有足够的经历和理解力,又有用不完的能量。
但她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个独自在宾馆里自杀的男人,那天他们互相陪伴了彼此 4 个小时,他没有死在电话线的那头,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接线员不应该过多地再去想起或者谈论起过去的案例。
赵子君一直留着他的电话,甚至还有他养父的电话,有时候赵子君想再回拨过去,或者想给他养父发个信息,但都会被同事或自己的理性制止,赵子君觉得他还会有自杀的风险,对死亡的恐惧让她没办法立刻转身忘记。
虽然他当下的悲伤被缓解了,但那个瞬间确实会产生任何蝴蝶效应吗,抑或是其实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人本身的痛苦,还是只能由他自己来面对吗?
这让赵子君困惑,她不知道挂掉电话之后,另一个空间会发生什么,这难免让她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但作为有经验的接线员,她又必须学会了正视人类的痛苦和无力,她需要继续自己的生活。
那是一个温暖而晴朗的夜晚,子君给我讲完这个故事已经快 12 点了,她结束了今晚的值班,我和她走在南昌街道两旁的臭椿树下,她推着电动车,回家有狗等着她,我记得她今晚对电话那头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祝你开心。
为保证病人隐私,文中所有提到的案例细节都进行了技术性的模糊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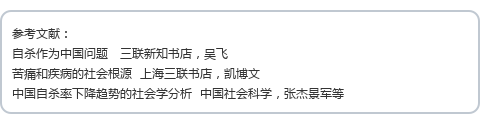
本文转载自丁香医生旗下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to-cure-sometimes),记录人和疾病、衰老和死亡的相处方式。

